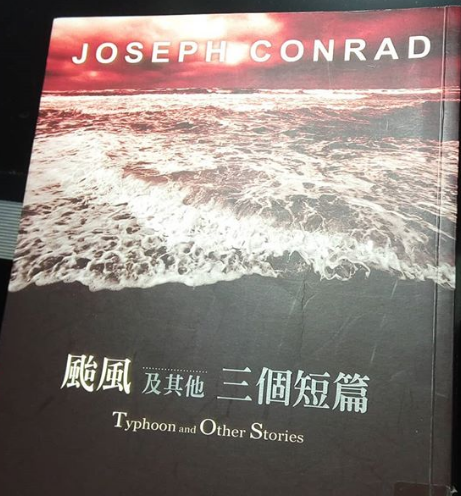藝術相關領域,美學是共通的,
美是哲學. Aesthetic 用在建築,音樂,繪畫,戲劇, 攝影, 皆通用.
美的形式
1 完整的形式
2 反覆的形式
3 漸層的形式
4 對稱的形式
5 平衡的形式
6 調和的形式
7 對比的形式
8 比例的形式
9 節奏的形式
10統一的形式
在音樂上, 曲式的優美也適用這樣的形式原則.

節錄部分訪談文字:
孔:有一件事情我一直覺得很奇怪,那個時候有很多人失蹤,很多人都說是被飛機載到太平洋丟掉了,到底是怎麼回事?
張:飛機的事我倒是沒有聽過,不過我知道有一個地方是專門處理犯人的,應該說是個「萬人塜」,那個洞很大很大,是用機器挖的,約有六、七十公尺長,是個圓的,有三層樓那樣高,上面有個蓋子,那個蓋子是用鋼筋水泥作的,上面舖了一層鐵皮,那個蓋子,就像馬路上的蓋子一樣,要把犯人丟下去時,蓋子就升上來了,裡面有很多很多的骨頭,臭得要死,我去過那個地方,也押解過人犯。
孔:那個地方在哪裡?
張:在新店往烏來那個方向, 這樣好了,我畫一個地圖給你看,比較清楚,你看,這不是屈尺路嗎?屈尺路再往前走,就有一座橋,然後再往前(新烏路)左邊的地方就可以看到一個軍營,這個軍營,在當時,約有三千多人,門口有衛兵把守,不准人參觀,曾經有百姓試圖蒐證,當場被衛兵射殺,那個洞,就是必須先從這個軍營進去,進去之後,來到後面有條山路,接著就是懸崖和峭壁,沿途有很多檢查站,把守甚嚴,然後左轉過來,就可以進入另一個軍營,那個洞,就在第二個軍營內,那個軍營,約有六千多人,而洞就在軍營的中間,這個洞,當年旁邊還有直升機停機坪,是用飛機直接載來的,不過後來怕人知道,才改用車輛接送人犯,那個洞的名字叫「河殺洞」,失蹤的人,應該是丟在那個地方。
孔:什麼時候挖的?
張:應該是保安司令部的時代吧?
孔:他們是怎麼處理人犯的?
張:人犯都是用繩子綁起來的,我有一次帶了三個人犯來,人犯帶來之後,蓋子就升起來了,臭得要命,我就把人犯交給了一個營長,那個營長是個老廣,他要把人犯踢下去時,都會先用廣東話罵一句「丟你老摸法海」,「天堂有路你不走,你要到地獄來」,一腳就踹下去了;接著第二個、第三個也都一樣,都是先罵那句廣東話,然後說「天堂」、「地獄」的話,一個一個都踹下去了。
孔:蓋子打開的時候,你有沒有看到還有活的?
張:有三個人,其他的統統是骨頭,臭得要死!
孔:那麼高會不會摔死啊?!
張:不會死,頂多是頸椎受傷,或是手腳骨折,不會死。
孔:那不是很慘嗎?
張:我聽到他們提到,在裡面的人,是「人吃人」的世界,只要一丟下去,底下的人就搶,因為他們餓壞了,也很渴,所以就吃他們的肉,喝他們的血,也有喊叫的聲音,不久之後,蓋子就蓋起來了。
但 "屈尺路嗎?屈尺路再往前走,就有一座橋,然後再往前(新烏路)左邊的地方就可以看到一個軍營"